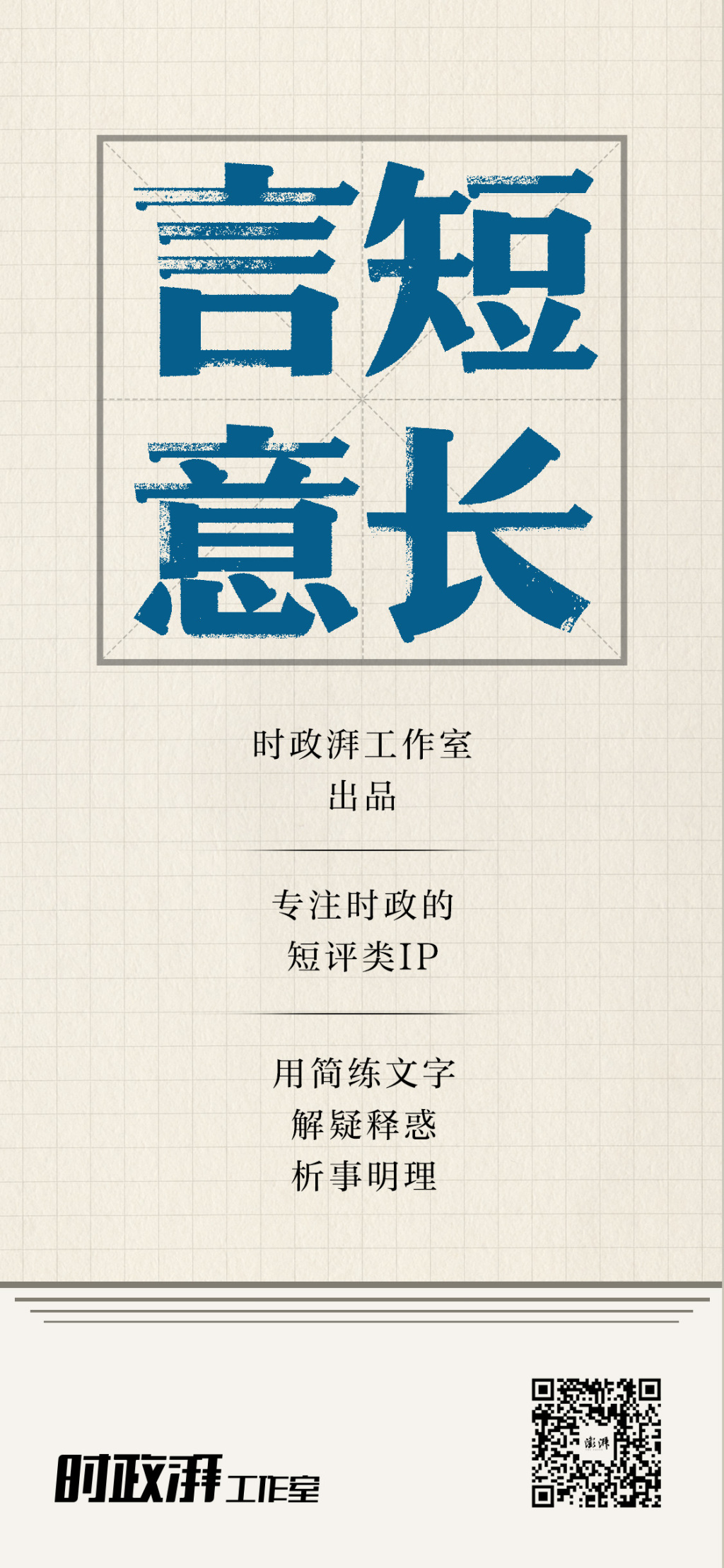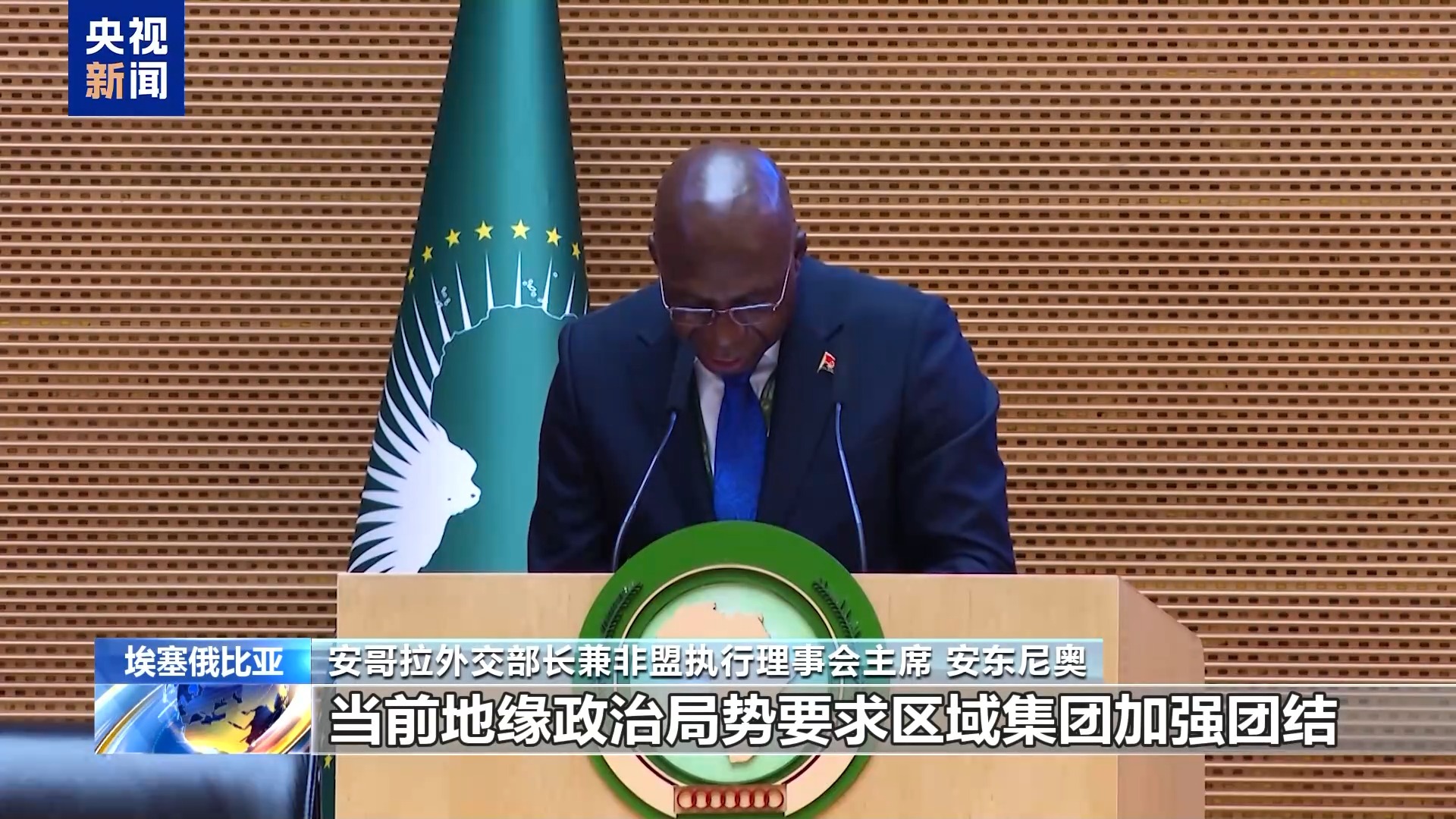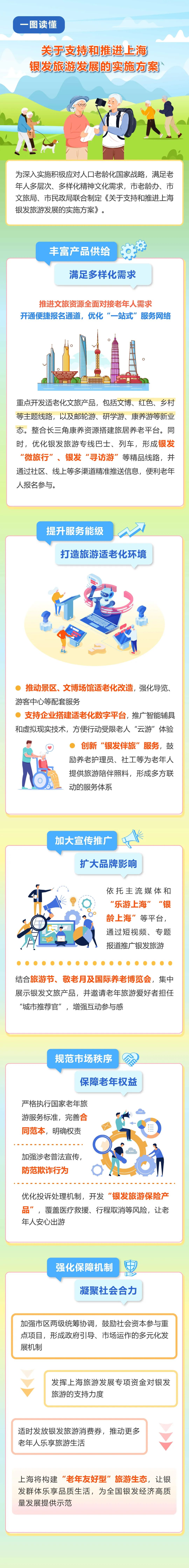精致优雅:近代早期英国的“文明礼仪”
对于任何有社会抱负的男男女女而言,了解上流社会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掌握优雅的餐桌礼仪。人们普遍认为,嘴里塞满食物、吃饭时吧唧嘴、舔盘子或在路边吃东西,都是粗俗之人的行为。12世纪,贝克尔斯的丹尼尔规定,和别人一起吃饭时,吐痰、咳嗽、擤鼻涕、舔手指或对着热汤吹气都是错误的行为。14世纪晚期,乔叟笔下的女修道院院长是一个讲求精致餐桌礼仪的典范。她从不让食物从手中滑落,也从不把手深深浸入酱汁;她时常擦拭嘴唇,这样她的杯子上就不会沾上食物的油脂。为每位食客提供单独的刀、叉、勺子和玻璃杯的现代习惯直到17世纪中期才开始被英格兰上流社会接受。之后又过了至少100年,这种习惯才在整个社会普及。一位作家在1673年感叹道:“外国人……指责我们用餐时……不用叉子而用手指。”在18世纪30年代以前,叉子十分少见,而且大多只在富裕家庭使用。直到18世纪中叶,人们还会把自己的刀带上餐桌。一本18世纪流行的笑话书讲述了在一次宴会上,一位莱斯特郡的农民从未见过叉子,别人让他用叉子,他也谢绝,问是否可以要一个没有任何槽口的勺子。1816年,一位埃塞克斯郡的农民用刀从烤鸡上取食一块肉,“不料却切到了同桌一位绅士的中指”。这起意外似乎是“因为一同就餐的人们急不可待,都同时将手伸进了烤盘”。
人们的社会等级虽有不同,但从餐桌礼仪上,我们看不出社会等级差别。17世纪末,一位在英国生活了十来年的胡格诺派难民注意到,英国人在餐桌上随时都可能打嗝,就像他们咳嗽和打喷嚏一样,不会在意别人的感受。一次,当因此受到指责时,一名英格兰男子要求知道,为什么在餐桌上除了吐痰和擤鼻涕之外,还要避免打嗝。在伊丽莎白时期,意大利人乔达诺·布鲁诺造访英格兰。他发现,尽管礼仪手册反对众人共用同一个酒器,但这种被反对的做法在英格兰仍长期存在,着实令他作呕。直到17世纪后期,富裕阶层才开始增加餐具的数量,禁止直接用手把食物放入口中,并且对任何别人嘴巴碰过的东西,也越来越厌恶。1671年,人们发现“有些人现在相当有洁癖”,只要看到别人用过的勺子没有擦,然后又直接夹菜,这些菜他们就不碰了。古文物研究者威廉·科尔曾在剑桥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接受教育。1765年访问巴黎时,他发现“法国人的一个做法值得借鉴”,就是给桌上每个人单独配平底玻璃杯或高脚酒杯。“这样就非常卫生,用餐者完全避免了使用别人用过的杯子的那种不好的感觉。”1784年,一名法国游客来到英国,发现桌上20个人都在用同一个大酒杯喝啤酒,这让他很反感。要知道早在两个多世纪前,乔瓦尼·德拉·卡萨的《加拉泰奥》就宣布禁止共享酒器,除非一同喝酒的人是相当要好的朋友。
18世纪初,不同社会阶层在餐桌礼仪上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一本配有插图的礼仪手册介绍道: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在端起酒杯时,手指放在酒杯柄上的位置就越低,端杯子的手指也越少。这本手册还对比了农民和贵妇使用勺子时的不同握法:前者是大拇指和其他手指一起上,后者则“用3个指尖……以一种赏心悦目的样子拿勺子”。餐具的使用习惯成了划分社会阶层的一个标志。1741年,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认为,“举止笨拙的家伙”有一个特点:他拿刀、叉和勺子的方式与其他人的不同。一位权威人士在1778年指出:“没有什么比吃相更能区分一位年轻绅士和一个粗俗小子了。”
切肉可体现重要的绅士风范,有其独特的规矩。1661年,一本烹饪书规定,在切肉时,一个人不能在肉的连接处放超过两个手指和一个拇指。1670年,据说“最讲究的切肉者”除了使用刀叉外,手根本不用碰肉。1716年,利奇菲尔德主教约翰·霍夫被人们描述为一位“相当出色的切肉者”。他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著称。据说在前一年(1715年),他还被邀请做坎特伯雷大主教。切斯特菲尔德勋爵非常重视“娴熟优雅的切肉方式,既不会围着块骨头削上半个小时,也不会将肉汁溅到周围人身上”。约翰·威尔克斯支持美国独立,因而在英国人看来是变节者。在1776年的一次宴会上,他展示自己精致的切肉技术,从而巴结当天的一些宾客。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便在其中,但他觉得这种款待有些让人煎熬。威尔克斯边切肉边说道:“先生,请允许我过去为您切一下肉……这块更好,色泽焦黄……先生,再来一块油脂更丰富的肉……接下来,来一些烤肉馅和肉汁……我很荣幸给您一些黄油……请允许我向您推荐一款鲜榨橙汁……或鲜榨柠檬汁,搭配烤肉也许更具风味。”
19世纪早期的礼仪书揭示了餐桌礼仪中错综复杂的细微差别,这些差别会引起最大程度的社交尴尬,从如何吃豌豆(使用甜点勺)等微妙的问题,到配汤餐包的大小。根据1836年的一部礼仪书的规定,餐包厚度不应小于1.5英寸。“没有什么比晚餐时供应的薄薄的餐包更让人掉价的了。”多年后,历史学家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1876-1962)也向他的孙子和孙女传达了这条规矩。关于礼仪的规矩发展的结果是,在餐桌礼仪方面,社会精英与平民百姓的差距越来越大。
整洁、干净是另一个衡量绅士风范的标准。原则上,这是每个人都该有的美德,因为它表示你尊重他人的感受。同时,这也是一种宗教义务,因为人体是上帝的创造物,应该受到相应的尊敬。正如虔敬的伊丽莎白·沃克在1689年告诉她孙子的那样,不是所有整洁、干净的人都是好人,但邋里邋遢的人当中好人不多。保持店面整洁、干净,对贸易也有好处。布料商人威廉·斯科特评论道,走进一家店,看见店主“站在痰液里,都快要被‘淹死’了”,这是多么令人作呕的一幕!
在现实生活中,整洁、干净被视为优越社会身份的标志。一位都铎王朝时期的权威人士建议,绅士应该在个人卫生方面“超越其他人”。而对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而言,没有什么比脏手和难看、参差不齐的指甲更粗俗不雅的了。于是他规定,绅士的指甲应保持“光滑和干净,而不是像平民百姓的指甲那样,总带着黑泥”。保持身体的清洁已成为一种社会标志。一位统计学家在1690年发现,社会等级越高的人,使用肥皂的次数就越多,换干净衣服的频率也越高。100年后,有人说“把自己打扮得干净精致……相比其他的外在修饰,更能彰显贵妇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
同样,社会差异也体现在了更私密的事情上。在某种程度上,隐藏身体的某些生理功能(主要指大小便)和私处是人们普遍希望的。长期以来,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认为大小便时旁若无人是一种冒犯的行为。公元前1世纪,看到人们对自己的生理功能存在羞耻感,一些犬儒主义哲学家嗤之以鼻,西塞罗却对这些哲学家的态度感到遗憾。他自己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身体的私处应该隐藏起来,本能的呼唤应该私下回应,公开谈论这些事情是不合适的。诺伯特·埃利亚斯认为,中世纪人对于“这些生理功能和暴露自己的私处,只是略有羞耻感或厌恶感”,因此“它们只受到轻微的排斥和约束”,这一观点肯定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些身体器官和相应的活动被大量的委婉语所包围,解决生理需求也通常在私下进行。正如“茅厕”(privy)一词的字面意思是“私密”,在修道院里,相关规则也很清楚。裸露是可耻的,据说就连“卑鄙的小丑”也会小心地遮掩自己的私处。
起初,人们强调下级在上级面前不得放肆,否则就是不够尊重上级或是不正当地利用与上级之间的信任关系。12世纪末,贝克尔斯的丹尼尔据此规定,名门的一家之长有权在正堂的洗手间里如厕,而其他人则得自己找个秘密的地方如厕,而且务必不暴露自己的私处。16世纪,乔瓦尼·德拉·卡萨的《加拉泰奥》虽然强调不要向友人暗示自己要如厕,但也指出,如果只有佣人和下级在场,主人不必遮掩自己的私处。一个世纪后,安托万·德·考廷也说过同样的话。然而,伊拉斯谟教导说,男孩应避免这种行为,因为即使没有其他人在场,天使总会在场。伊丽莎白时代的军事指挥官和贵族蒙特乔伊勋爵,在解决内急时表现得相当低调稳重,因此受到好评:“即使身处自己的私人房间,当着好友的面,他也从不会去解决内急。也许唯一的例外发生在他征战爱尔兰时,因为他实在找不到洗手间。”虔敬的尼古拉斯·费拉尔认为,一个人“在如厕时应该非常低调稳重”。他对“我们所处时代的这个民族在如厕行为上的厚颜无耻”感到震惊,认为与其他国家的做法相比,简直不法忍受。
他这么说是因为尽管英国上流社会人士会找隐蔽的地方解决内急,但对于那个地方究竟适不适合如厕,他们远远不够慎重。詹姆斯一世打猎时整天坐在马鞍上(也就在马鞍上解决内急)。塞缪尔·佩皮斯有一次在烟囱里大便。1665-1666年,当英国议会在牛津召开会议时,查理二世的朝臣们将粪便留在了“烟囱、书房、煤库、地窖里的每个角落”。说起“有些不拘小节的神学家”乔赛亚·普伦(1631-1714),还有一段趣闻。普伦是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副院长,一天,他带领一众贵妇参观牛津大学,并牵着其中最显赫的一位女士的手。突然,他想如厕,就做了一个手势。然后,“他转身对着墙,就开始小便了,而牵着女士的手还攥得紧紧的,这让对方好生难堪”。直到1751年,一位作家才声称:“女性无论多么着急和不适,都不会不知羞耻地随地大小便。因此对于男性来说,站在街上,面对墙壁,甚至当着女人的面就解决内急,实属不雅。”
16世纪90年代,一位旅行家指出,“我们的(英格兰)女人就连上厕所都不愿让别人察觉,而荷兰莱顿市的‘年轻女子’竟然不知羞耻地当街大小便”。17世纪中叶,医学作家开始担心,有些人觉得跟同伴说自己要如厕是一件非常难为情的事,所以他们就憋着,甚至危及了自己的健康。据说,一些人因此丧命,还有一些人,尤其当着女性的面“不好意思去上厕所,结果落下了无法治愈的病。憋尿真的很危险”。一位18世纪的旅行家说,英国的女士即使被人看到去上厕所,也会羞怯难当。“然而据我所知,荷兰有一位老妇人,就在一位男士旁边的一个坑上如厕(男女同厕)。完事后,她用青口贝的贝壳擦拭干净,再用一个铲子,礼貌地将用过的这个贝壳递给旁边的男士使用。”
即使男人当街小便,也分体面和不雅两种方式。路人应假装没看见这种行为,同伴们应脱下帽子,站在其身后为那个男人挡着。对有些人来说,这些措施还不够。正如诗人约翰·盖伊在1716年所敦促的:
讲点文明,找个秘密的角落行事,
别让路过的少女面红耳赤。
18世纪的哲学家大卫·哈特利认为,“由于受到教育、习俗以及父母和学校训诫的影响,人们对于‘露天如厕’的羞耻感大大增加了”。从1669年起,在宫廷里,“国王坐便器的擦洗者”(服侍国王排便的内官),被越来越委婉地称为“衣带官”。而到了汉诺威时代,在这类隐秘的场合,这一职位不再出现。1732年,马尔伯勒公爵夫人莎拉·丘吉尔到斯卡伯勒泡温泉做水疗,在谈到此次经历时,她指出其他人与贵族在生活习惯上存在差距。品尝温泉、泡温泉之后,女人们开始有了便意,于是被领进一个房间。有人说:“房里有20多个洞,一旁有人提供干净裤衩。所有人就这么聚在一起,大眼瞪小眼地用一种舒适的姿势解决内急。众人离开后,在房间门口,堆积了一大堆她们用来擦拭的树叶……我快马加鞭回到家里,生怕被逼进那个群体。”18世纪的餐具柜还放着尿壶。当着其他食客和自己同僚的面,绅士可以安然地使用这些器皿。然而,注重面子的诺福克牧师詹姆斯·伍德福德是他那个阶层和年龄段人士的典型。他叫人在花园中竖起一块挡板,防止厨房里的佣人“看到谁又去如厕了”。
诺伯特·埃利亚斯发现在近代早期,“人们在公共场合,越来越注意去除或遮掩一些可能引发他人不适的生理行为”。他的这一观察很敏锐。1703年,一位重新翻译乔瓦尼·德拉·卡萨的《加拉泰奥》一书的译者心满意足地指出,他所处时代的人已经认识到某些行为是不雅的,尽管在近150年前,在当时“世界上最有礼貌的国家”,这些行为早已被认为不雅。1774年,该书的另一位译者指出:现在看来,《加拉泰奥》中的许多告诫是“荒谬的”,因为它们告诫人们不要有“在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不可能有的不道德行为”。几年后,塞缪尔·约翰逊评论道,如果读卡斯蒂廖内和乔瓦尼·德拉·卡萨作品的人比以前少了,“那只是因为作者所希望的改革已经实现了,书中的告诫现在已不合时宜”。
然而,有些习惯却迟迟无法摒弃。1533年,在亨利八世的王后安妮·博林的加冕宴会上,“当博林斜侧身子吐痰时”,两位侍女在她面前拉起一块遮布,这也是她加冕为王后的一种待遇。1661年,有一次塞缪尔·佩皮斯去看戏,一位女士“不小心”朝身后吐了一口痰,正好落在他身上(“但见她如花似玉,我一点也不气恼”)。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旅行家法因斯·莫里森认为很卓尔不群的一件事是,在奥斯曼土耳其的清真寺里,随地吐痰是一种“不小的罪过”。而在1678年,一位作家认为,荷兰人在房间角落里放一壶沙子当痰盂,证明了他们特别讲究卫生。“我的朋友可以在我稀罕的地板上吐痰。”诗人乔治·赫伯特在17世纪30年代初吟诵道。然而100年后,随着地毯的普及,这种行为将是对友谊的严峻考验。
上流社会也因其独特的语言习惯而与众不同。18世纪的一位修辞学权威人士认为,“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存在两种方言:一种是得体的方言,另一种是低俗的方言。而事实上,方言有很多种,地区差异和社会等级差异导致了众多各具特色的口音、语法和词语。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伊顿公学的校长认为“最好、最纯正的英语”在伦敦。伊丽莎白时代的专家乔治·帕特纳姆也将宫廷或“发达城镇”的人们所说的英语与“外国人经过的边陲或港口小镇”的人们说的英语做了对比。与帕特纳姆近乎同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威廉·卡姆登说:“我们有宫廷和乡村英语、北方和南方英语、常规和粗俗英语。”乡下人的话一再被贬损为“粗鲁、野蛮”。托马斯·霍布斯指出,方言千千万万种,但一成不变的是,“下层民众的方言……总是有别于宫廷语言的”。
在近代早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伦敦以外的发音和外地方言视为“不文明”的。帕特纳姆宣称,“在王国的高地村庄(苏格兰)和角落,只有穷人、乡巴佬和不文明的人”。这些人“通过奇怪的口音、畸形的发音方式和错误的拼字法”,亵渎了语言。在他看来,语言标准应由“有礼貌、有教养的人”来制定。无独有偶,1597年,伯里·圣埃德蒙兹学校的校长萨福克告诫学生,远离“乡下人的污言秽语”。维尼家族是17世纪的名门望族,却拒不使用当地白金汉郡的方言。到了18世纪后期,语言向标准发音方向的发展愈演愈烈,而且变得相当规范。一位演讲大师在1762年断言:除了宫廷中流行的语言,其他方言是“狭隘、土气、迂腐、呆板教育的确凿体现”,如果继续说这类方言,就是自取其辱。1783年,另一位自称专家的人宣称:“我……觉得理所当然的是,想让自己的朗读和讲话听起来悦耳,首要前提是不受地方口音的影响。”在那个年代,人们仅凭衣着,不再容易区分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人们认为,“纯正和礼貌的言语”是划分绅士与贴身男仆、淑女与女裁缝之间仅存的外在区别。人们一直认为,语言使用上的差异是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之一。而且,如果人们想保持自己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非常自律。
优雅的谈话是礼貌的典范。大卫·休谟声称,正是“为了使谈话和思想交流更加轻松愉悦”,“良好的礼仪”才被创造出来。在他所处的时代,“交谈”一词仍然可以指任何形式的社交活动,但是人们早已知道它的狭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交流。在伊丽莎白时代,众所周知,“话语与交谈”是“朝臣生活的主要目标”。17世纪,交谈成了“有教养之人最大的乐趣”。正是在谈话中,交谈者展示着他们的“礼貌或文雅”。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言语带来的愉悦”,但很快就成了文明礼貌行为的同义词。到了18世纪,丹尼尔·笛福把交谈视为“生命中最光彩照人的部分”。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方便人们交流的场所和形式:咖啡馆、俱乐部、社团协会、集会厅、社交性拜访和晚宴等。18世纪后期的一位随笔作家指出,“每个人在形影相吊时,出于自怜自爱,会本能地对他人粗鲁无礼、不管不顾。而在平等基础上融入社会不仅是摆脱这种本能的唯一途径,而且能培养温文尔雅的举止,以及对他人的体恤关怀。这些构成了社交生活的最高乐趣,现如今被称为‘礼貌或文雅’”。
彬彬有礼的谈话,究其目的而言,与其说是传递信息,不如说是从和睦相处中得到快乐和分享快乐。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得风趣幽默,不随意打断别人讲话,不恶意散布流言蜚语,不自吹自擂、卖弄学问,避开机械呆板或颇具争议的话题。如果谈话者必须反驳他人,要很有礼貌,避免因分歧伤了和气。尽管人们交流时应避免阿谀奉承,但也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向对方表达高度的尊重。为此,正如当时的某个人在1632年所说,“一种被称为‘恭维’的新的语言艺术已经创造出来了”。
“恭维”一词原本指代所有恭敬礼貌的行为,但逐渐演变成专用来赞美和致敬的礼貌表达。17世纪出版的众多的“谈话技巧”类图书,对交谈中如何引经据典、对答如流给出了建议。同时,这些书也指导人们如何准确地使用恭维语。一位观察家指出,有些人专门学习“如何赞美他人”,而这种做法并没有逃过当代讽刺作家的眼睛。按照现代标准,相关图书所推荐的溢美之词,明显花里胡哨。至于那些指导人们如何写信的手册(书信其实也是一种谈话形式),它们同样建议使用溢美之词,如“您最忠诚、最卑微的仆人”,“最愿意为您效劳的人”,“永远爱您、为您服务的人”。然而,习俗却在不断变化。1609年,一位法国作家告诉英国读者,再用“上帝保佑您健康”作为写信的开头语,是“愚蠢可笑的”。
在礼貌的上流社会,禁止谈论贬低他人社会地位的话题。比如,人们不应谈论生意,因为对于那些假装自己不是商人的人,谈论本行是不可接受的。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也不应谈论天气,因为许多人的生计依赖天气的变幻莫测。有人在1716年说,谈论天气是“低贱、卑鄙和没教养的行为”。“有教养的人”永远不谈论自己的妻子,这是一条铁律。同样,妇女也被劝诫,不要谈论彼此的家事、孩子或服饰。所有个人问题都应避免被谈论。1670年,有位作家建议:“当你动了番脑筋,想好和别人聊什么时,记得只谈事、不谈人。”流言蜚语潜在的破坏性太大。同样,“过激的豪言壮语”也被认为是“有失体统”的言语。良好的教养对交谈的首要要求是“轻松愉悦、不冒犯人”。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与马尔伯勒公爵夫人的关系不怎么好。1725年,在谈起这件事时,蒙塔古夫人说:“我们仍有来往,即使讨厌对方,也坚决保持礼貌。”
人们很少不折不扣地遵守文明谈话的规则,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因为太多时候,人类的虚荣心、利己主义、好斗和不耐烦会掺杂在谈话中。同样,很多时候人们忍不住要去开别人的玩笑,尽管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别人,因为人们喜欢“调侃”。即便如此,上流社会在交谈方式上也与普通阶层大相径庭。有教养之人始终坚持,“在任何场合与人交谈时,都要比乡下人、未受过教育的人更文明礼貌”。约瑟夫·艾迪生在1711年抱怨说,有些“城里人,尤其是那些在法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喜欢用我们语言中最粗俗、最不文明的词语”。他还认为,有教养之人应该使用“谦虚稳重”的表达方式,而把“家常话”留给庸俗之人。
总之,语言变得更加优雅。塞缪尔·约翰逊指出:“随着礼貌程度的提高,对于那些精致而有品位的人而言,有些表达方式显得过于粗俗不雅。”1768年,女学者伊丽莎白·卡特吃惊地发现,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就连“最伟大的人物”的信件也包含着“如今社会最底层的人都难以接受的表达方式”。16世纪初,语法学家约翰·斯坦布里奇为小学生编写了拉丁语教科书。然而200年后,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却不会逼自己的儿子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直截了当地将解剖学术语从拉丁语翻译成了英语。就连地方法院出庭的证人都不会出声念这些术语,而是把它们写在纸条上传递,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亚当·斯密认为,“生活在一个非常文明的社会中,人最应景的一种特征是‘精致敏感’,而这总会推动上流社会人士变得愈发委婉和高贵”。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礼貌准则在人们的生活中开始独树一帜。它们强化了贵族统治,但也要求贵族遵守社会盛行的习俗。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一位讽刺作家声称,一个腰缠万贯之人,无论其行为多么不堪,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尊敬和礼遇(如脱帽礼和屈膝礼)”,财富果真能弥补很多不足。但在现实生活中,富人通常也需要像其他人一样学会礼貌待人。纽卡斯尔侯爵(后来成为公爵)威廉·卡文迪什抱怨说,查理一世的宫廷对时尚的追求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比如,宫廷人士认为,从巴黎来的舞者随时展现近一个月的法国的时尚礼仪。如果不去跟风学会这些礼仪,就连英国最显赫的贵族都会被嘲笑。
在现实生活中,礼仪等级和社会等级从来没有完全重合过。有时,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是礼仪作家寄予希望的礼仪典范,比如以下诸位。第一位是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沃尔特·德弗罗(1539-1576)。他用一种特殊的风度待人接物,无论面对上级、平级还是下级,他都文质彬彬、坦诚相待,不愧为贵族的典范。第二位是第二代阿伦德尔伯爵托马斯·霍华德(1586-1646)。他文雅从容、步态稳重,虽然衣着朴素,但他无论去哪里,都会令人觉得他气度不凡。第三位是肯尼尔姆·迪格比爵士(1603-1665)。他“举止优雅、彬彬有礼、能言善辩,总能带给人惊喜”。第四位是18世纪的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1650-1722)。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写道,丘吉尔体格健硕、气宇轩昂,“无论男女都对他无法抗拒”。正是这种“风度翩翩的举止”,使他能让奥格斯堡同盟(Grand Alliance)最终战胜法王路易十四。作家、政治家和收藏家霍勒斯·沃波尔(1717-1797)是礼貌高雅的典型代表。“他每次走进房间,都带着一股清新优雅的时尚之风——他脱下帽子后,或把帽子合于双手之间,或夹在胳膊之下。他膝盖略弯曲,脚尖触地,生怕地面湿滑一般,尽显谦恭之态。”
然而,尽管通过“优雅的举止、轻松的谈吐和彬彬有礼、乐于助人的风度”来凸显自己的主要是来自上流社会的人士,但不乏一些原本来自社会下层的新贵成功掌握了上流社会的那套举止礼仪。当然也有一些人虽然位高权重,但缺乏教养、言语粗俗、习性龌龊。在英国内战前,格洛斯特主教戈弗雷·古德曼对人类天性中动物的一面深恶痛绝。一次他宣称:“在所有令人厌恶的气味中,没有哪种比人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更让人难以忍受。”然而在1638年,弗朗西斯·温德班克爵士发现古德曼主教因为其母亲去世而哭泣,却没有用手帕来擦眼泪和鼻涕。“主教大人直接用手擦拭眼泪和鼻涕,然后在他的天鹅绒大衣上擦了擦手……我承认,看到这一幕,我对他失去了不少同情心。”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小说家理查德·格雷夫斯声称曾目睹各种令人尴尬的情形:一位乡村绅士向别人借了牙签,用了一下还给别人,说了声谢谢;一位受人尊敬的市长,在公共场合大声咳痰,令旁人大吃一惊;一位知名的医生把痰吐到别人家地毯上;一位富商内急,当众找了些废纸,从中间挑了一张最柔软的塞进口袋。
如果你想了解名人有多么频繁地不遵守礼貌举止的最高准则,只需读一读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对他那个时代一些主要政治家的评论: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举止不雅”;汤森勋爵“举止粗鲁、土气,他看似性情乖戾”;纽卡斯尔公爵“整天行色匆匆,从不走路,总在小跑”;贝德福德公爵“既不会也不想取悦他人”;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言语不雅,说话迟疑,口才拙劣”。
此外,在上流社会,时不时会出现一批目无法纪、肆无忌惮、崇尚暴力和猥亵行为的小混混。关于他们,有很多称呼:“威吓者”、“自吹自擂者”、“勇闯天涯者”、“招摇过市者”、“咆哮男孩”、“酒后喧闹者”、“敢死队”、“浪子”、“街头暴徒”,以及“目中无人、烂醉如泥的恶魔之子”等。这类人无耻地宣称自己的社会优越感不是通过遵守既定的文明礼仪而获得的;相反,他们通过蓄意藐视和违反社会规约来彰显其社会优越感。查理二世的朝臣们尤其以酗酒、放荡的性行为和崇尚自由享乐主义而臭名昭著。一些大学生因暴力、酗酒、滥交和夜间寻衅滋事而堕落成了反主流文化的群体。良好的行为准则建立得越牢固,他们越轨的快感就越强烈。1667年,在圣乔治日仪式结束当天,主办方用丰盛的晚宴招待国王和受封嘉德勋章的骑士们。可就在这么隆重庄严的场合,客人们却起了争执,开始“尽情地”相互投掷“宴会用品”,俨然将宴会变成了“竞技场”。约翰·伊夫林“由于担心局面失控”落荒而逃。1696年,一位到阿姆斯特丹的英格兰游客惊奇地发现,荷兰城市与伦敦在夜间截然不同。这里“没有打架斗殴,也没有头破血流的人;没有巡夜的人,也没有行凶者;没有剑拔弩张的情形,也没有人被扭送到看守所过夜;没有砸窗盗窃行为,也没有扯下广告牌或踢倒理发店广告柱等破坏公物的行为”。
17世纪后期,英国的礼貌规范与日俱增,同时色情作品开始出现。18世纪,与良好教养同时出现的是性解放、酗酒、野蛮凶险的体育竞技、淫秽下流的幽默和无耻的流言蜚语。然而英国社会的光明面与黑暗面的交融并非巧合。文明礼貌的价值观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无处不在,但它们对上流社会行为的影响从未完全体现出来。

(本文摘自基思·托马斯著《文明的追求:现代英国的礼仪与文化探源》,戴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相关文章
陈宝良:明清时期少林、武当两派的拳法
编年岂徒哉:《资治通鉴》中魏征26年的人生史
美空军B-1B轰炸机抵达日本,执行战略威慑任务
业绩激活新消费,押中爆款哪吒IP的泛娱乐龙头卡游再冲港股IPO
锦州4名少年偷手机89部还发视频炫耀,店主:贼抓了又放,手机向谁要
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16日晚开始发生地磁暴,尚未结束
上海出台26项措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关于公平竞争、融资支持等
4个“首”,江西这场大会将引爆“诗和远方”
言短意长|郑州大学教授范冰冰遭遇标题党
广西京族人的“高跷捞虾”:以前老辈个个都会,现在展演收入赶得上真捕鱼
独家专访|阿来:人只活几十年,我得写点不一样的
眨眼间能完成10亿次存储,上海科研团队研制出超高速闪存
是什么,坚定了外资企业“在浦东为世界”的决心?
对话|女足国脚,离开体制“再就业”
非盟特别会议聚焦美国关税政策,共商应对之法
“努力稳住外贸基本盘”,浙江省委书记、省长接连调研外贸
美联储主席警告关税影响,纳指跌超3%,黄金续创历史新高
上海:文旅资源全面对接老年人需求,创新“银发伴旅”服务
奥园集团:截至3月底逾期债务约438.33亿元
丝路枢纽“扩容”,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启用新航站楼
- 公安机关依法严打危害生态和生物安全犯罪,公布一批典型案例
- 国家药监局通告18批次化妆品检出禁用原料,含婴儿护肤霜
- 经济日报刊文:从康养旅居看银发经济
- 又一上海出品力作开播!孙俪再演职场丽人
- 煤矿疑污水渗漏致数十亩耕地被淹,陕西榆阳区:成立调查组调查
- 正义网评“一男两女举办婚礼”:“一夫多妻”流量闹剧该歇了
- 伊朗外长: 下一轮伊美核问题谈判将于26日举行
- 对话|棋后居文君:创造历史之后,还有继续追梦的心
- 韩国一战机飞行训练中掉落机炮吊舱和空油箱
- 观察|中日航线加速扩容,航空公司如何抓住机会?
- 85岁眼科专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原眼科主任喻长泰逝世
- 解除近70家煤电厂有毒物质排放限制,特朗普能重振煤炭吗?